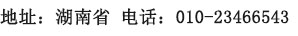梅的好
王祥夫
古人品花,梅为第一品。人人都知道冬天必将会过去,谁也没见过留在那里不肯走的冬天。但冬天尚未离开春天还没到来的时候,就在这个小小的夹缝里,梅花冲风冒雪地开了,花朵是小的,我认为梅花应该小,瘦瘦小小才见风致。尝见有的画家画大幅红梅,千朵万朵拥挤在一起像是着了火,是不得梅花之真趣!梅花从开到谢,可以说是极为短暂的,简直是须臾间的事,苏东坡的那首诗:“夜深只恐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明明知道他是在写海棠,而我偏偏认为那是写给梅花的,这样好的诗句,苏东坡怎么会写给海棠?我总是认为一切好的诗句都应该写给梅花。梅花若从颜色上分,红梅、粉梅、绿梅、白梅。好像也只有这四种。中国人干什么事情都喜欢排座次。《水浒》中一百单八个英雄居然个个都排到,一排一排前前后后地坐,就是不肯大家都坐一排或混坐,混坐其实最平等,我喜欢到大澡堂洗澡便如此,大家欢欢喜喜赤诚相见,管他谁长谁短!再说到梅花,你就无法给它们排座次,红、白、粉、绿我认为都好,各有各的风韵。梅花是,全开的时候好,半开的时候也好,各有各的好。梅花开的时候,小小的花苞从米粒那么大慢慢大到*豆大要经过多少风风雨雨,梅花也知道不莽撞才好,花开的时候先要让花蕊吐出来试探一下,古人画梅,尝见花骨朵上只点一蕊。风寒中的梅便是这样,先探出蕊来,这就和其他花不一样,然后才一点一点开起来,一旦开起来便不再犹豫,直至大放。谁见过开到一半又羞答答合拢的梅花?还有,许多事情都是有衬托才好,梅花却偏不要衬托,叶子是后来的事,把花开完了再说,所以梅花真是可爱。桃花却要手拉着绿叶一起登场,红红绿绿固然热闹,却不能像梅花那样让人感动。除了梅花,还有什么花敢于冲风冒雪地绽放?还有什么花能在风寒中抖擞它的那一缕刻骨的清香?这清香,便是最好的宣言,也只有在料峭的风寒里你才会读出梅的好。
舒服的尺度
乔叶
有一次,我受邀担当某个“最美读书声”活动的决赛评委,对于朗诵我是外行,所以只对朗诵内容做了些微阐释。至于对朗诵本身的直觉感受,自然有不少喜欢的,却也有不少让我如坐针毡。近些年,读书之风日盛,我参加过不少类似活动,一方面为全民读书潮欣悦,一方面又有隐隐担心。读书几乎成了朗诵的代名词,而朗诵又越来越偏重于表演。比如有标新立异者,朗诵红*过草地的篇章就穿着红*服,朗诵李白的诗篇就穿仙袂飘飘的唐装,在声调上的处理也很花哨,或者声嘶力竭,或者声音颤抖故作哽咽,或者满台子跑来跑去边跑边喊,或者竟然唱了起来。说实话,这些带给我的不适感,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
“这些花活儿有用吗?没用的。但凡是艺术,都有一个基本尺度,我认为最朴素最有效的尺度就是:要让人舒服。”突然,听到其中一位评委如此点评,顿时被击中。
他是省里的朗诵名家。我曾听过他几次朗诵,每次都觉得很好。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评价。现在,终于知道了,就是舒服。又想,也许很多人和我一样吧,可以不懂某个专业,但是舒服不舒服,却是可以体会到的。
让人舒服,这个尺度初听觉得意外,再一品就觉得很在情理之中。
让人舒服,这个尺度意味着什么?
意味着懂得。比如按摩师为你按摩的时候,你之所以会觉得舒服,是因为他懂得你的所有骨头和肌肉。
意味着理解。比如上身后既好看又舒服的衣服,那是因为设计师充分地理解衣料的材质,也充分理解穿衣者的身体。
也意味着缜密的逻辑。情感逻辑,审美逻辑,都要坚实。因此好的画,好的音乐,都是让人舒服的。
这么想来,让人舒服意味的还真多啊。她意味着自然,最大程度的自然。她还意味着体贴。体贴人心,体贴世情。她甚至意味着科学的优美和精确,因此哪怕是*金分割点,也会是让你舒服的点。
当然,让人舒服,不是讨好,不是谄媚。让人舒服,也不是说要拒绝夸张。有很多夸张也会让你很舒服。漫画夸张吧?花腔女高音夸张吧?京剧表演夸张吧?夸张得合适时,就会让你觉得很舒服。
让人舒服更不等同于自己随意。自由之前先自律。你看体操表演,流畅,优美,看着那么舒服。谁都知道表演的人在背后下了非同寻常的苦功。写作当然也是如此。当你读某篇文章觉得特别舒服的时候,你难以想象作者为一句话,为一个题目,琢磨了多少次。——驾驭的时候不显得艰难,是因为背后严苛的训练。只有经过沉默的努力,才可能会有明亮的呈现。功夫下得越足,临场才可能越轻松,也才会在呈现的时候让人舒服。
所以,某些朗诵为什么会让人不舒服?要么就是在做不高级的苦情戏,实际上就是对受众进行强制绑架。要么就是哗众取宠,这更是一种试图吸引眼球的幼稚伎俩。他们没有把真正的功夫浸入到文本的字里行间、一呼一吸、一停一顿中,更没有浸入到情感深处。他们的努力都漂浮在外壳,怎么会把别人带进内核中呢?怎么可能会让人舒服呢?即使他们看起来是如此努力。而有意思的是,所有外在的虚张声势,恰恰就是因为内里弱,没别的。
第一等画
陆春祥
洪迈的《夷坚乙志》卷第五有《画学生》,第一等画的立意让人耳目一新。
成都郫县百姓王道亨,七岁时就能画画,笔法、立意,都有过人之处。*和年间(公元年—年),朝廷开设画学专科,考试仿照太学的方法,全国各地优秀的画工集中考试,优秀者录用。王道亨参加了第一批考试,题目是根据唐人的两句诗作画:蝴蝶梦中家万里,子规枝上月三更。
王道亨交上来的画,意境是这样的:苏武在北海边牧羊,盖着毛毯卧着,手上捏着符节,有两只蝴蝶在他面前飞舞,那种在沙漠上、风雪里羁旅愁苦的酸楚,让人泪目。另外,王道亨又画了扶疏的林木,上有杜鹃,午夜时分,月亮当空,树影照地,亭榭楼观,皆隐约可见。
无疑,王道亨得了第一名。次日,王的画被送到宋徽宗面前,皇帝一看,大为惊奇,立即升王做了画学录。
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,说的是诗画相通,而相通,无非是独特的意境。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笑”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“独钓寒江雪”“古道西风瘦马”,所有的好诗词,都有意境突出的好画面。
宋朝邓椿的《画继》,有两个创意的例子颇为有名。
一个是战德淳,画院的考试题是“蝴蝶梦中家万里”,他画是的苏武牧羊假寐以见万里意,得了第一名。
又有另外一次考试的第一名,试题是“野水无人渡,孤舟尽日横”,第二名以下的画意,大部分都是岸边一只空船,有的船上有白鹭停在舱舷间,有的船篷上有乌鸦停着,第一名的画,意境是这样的:一人卧于船尾,横一孤笛。他的构思,不是没有船工,只是没有行人,船工的闲正好反衬河渡的孤。
中国汉字具有画一般的奇特,是因为先民创造的象形文字,本身就是画。只要我们细品,好的词语都具有这种强烈的画面感。
《庄子养生主》“庖丁解牛”一节,那个高明的厨师,一把杀牛刀用了十九年,竟然一点也不钝,依然锋利,看他解完牛后的神态:“提刀四顾,为之踌躇满志”。踌躇满志,现在早已凝固成特定的意义,但在这里,你可以看到一个为自己技艺而骄傲的厨师,这种骄傲程度甚至已经目中无人,天下的厨师,像我这样的,恐怕再也没有了。是的,仅从这个词语上,那个庖丁已经在读者脑中名垂千古了。而庄子,正是通过著名厨师的技艺,告诉人们,道是怎么一回事。
杜牧的《旅宿》,描写离家久远的游子,一个人独自在旅馆的心情,有这样两句:“寒灯思旧事,断雁警愁眠”。这“寒灯”,看得人心都有点发毛,“灯”肯定不会寒,不仅不寒,还会发出温暖的光,但是,孤寂的旅人,离群的大雁,它们的生动画面,都靠“寒灯”打开。
杜甫的名诗《兵车行》开头,简直就是一幅大叙事画:“车辚辚,马萧萧,行人弓箭各在腰。爷娘妻子走相送,尘埃不见咸阳桥”。然后,撕心裂肺的场景紧接而来:“停车顿足拦道哭”,七个字,四个动作,官家的连年征战,百姓的苦不堪言,生离死别的场景,让人动容,那种哭声,一人哭,一家哭,众人哭,哭声汇成巨大的气流,直上云霄。
王道亨的画,意境如此别致,一定离不开他扎实的诗文基础,否则,再好的画技,画也只是枯燥呆板的花纸而已。
山子
厚圃
吾乡樟林有清代名园西塘,集住宅、书斋、庭园三者于一体,亭榭楼阁,莲池白塔,主景为太湖石叠石造山,石壁上凿着“秋水长天”四字,取自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,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少时若要照相,父母便把我们领至西塘取景。当初只觉得假山好看,却不明白它所涵藏的真正意义。
陈继儒在《小窗游记》中说过:“古之君子,行无友,则友松竹;居无友,则友云山。余无友,则友古之友松竹、友云山者。”古代富庶的文人,爱将山石搬进自己的庭院,营造咫尺山林的意境,以追求天然之趣。小块的山石也被文人们随手带进雅室,与经史、香炉、古琴、笔砚一块搁于书案条几之上,一拳之大浓缩三山五岳,方寸之间展露气象万千。文人们朝夕游息其间,人与物相互浸润,以求得心清意远,抵达天人合一之境。
赵希鹄的《洞天清录》有怪石辨,“怪石小而起峰,多有岩岫耸秀嵚嵌之状,可登几案观玩,亦奇物也”这应该就是“山子”的原义,后来又扩展到用竹木牙角、玉石陶瓷等各种材质来制作雕琢的摆件,比如笔架也属此列。记得小时我家有一座寿山石山子,一拃多高,外形呈峰峦状,上边雕刻着花花草草,大热天我爱偷偷抚摸它,从细腻的石质中寻得一丝凉爽的触感。后来我家搬了新居,那座山子从此不知去向。
一般说来,文人赏石、藏石的雅好盛行于唐宋,晚唐画家孙位的唯一传世之作《高逸图》,或者宋徽宗赵佶的《祥龙石图》,都有奇石的身影。到了明代后期,随着《素园石谱》一书的问世,文人对奇石的收藏似乎进入了高峰期。我的书案上有段时间搁着一本《素园石谱》,属于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“古刻新韵”系列,石谱本身绘制精美,印刷也好,苦读之余翻翻,颇能一浣浊眼放松心情,至于说那是李后主的砚山、苏轼的雪浪石或者米芾的研山写真,就不必去较那个真了。
我父母爱石也藏石,旧宅“醉园”有大大小小的奇石不下千块。我的两个妹妹或者关系密切的亲友乔迁,我父亲就会割爱送一座山子给他们,就算对方不懂赏石,至少也明白它能起到“石敢当”那样驱邪镇宅的作用。几年前我带着父母去美国,在纽约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,于二楼的露台意外地见到一个仿中国苏州园林风格的景观,“泠泉亭”里摆着一方四尺有余的灵璧石,配以苏工底座,亭子四周湖石堆砌,室内的几案上也摆着梅瓶枯枝笔筒山子,有一方皮色灰白的湖石孔洞贯通温润古雅,至今让人难忘。
我在深圳的家里藏着好几座山子,太湖石、灵璧石、戈壁石等石种,画案几桌书架博古架上随意摆放,隔一段时间也会换换,夏天到了,在山子侧旁搁一器皿,养一朵莲花。秋天来了,往一只青釉开片的盘子里放几枚小巧的佛手。接近岁末,养一两盆水仙,再在山子前搁几只*澄澄的潮州柑,算是岁朝清供。古人讲究清供,就是把文玩、卉石、瓜果置于案头以供观赏,若是有收藏的岁朝清供图,也可张挂出来,为草枯风寒的岁末年初增添一缕喜气和暖意。
我的书桌上还摆着一方广西大化石,为好朋友所转让,比沙田柚要大些,外形也有点像,色彩明丽石质细腻如小儿肌肤,经过经年累月的摩挲抚玩,表面更是明亮如珠。我不知道它算不算山子,我总以为山子还是应该有着峰峦的样貌,哪像它形如柚子,其实也不太像柚子,似乎更像一个收束了口子的钱袋,若有人再问我它的名字,就叫“代代平安”好了。
陶辛水韵之美
梅桑榆
芜湖市湾沚区陶辛镇,东濒青弋江,南临资福河,四面环水,且多圩区,而国家4A级旅游景区“陶辛水韵”最为广大,水域达80多平方公里,其中有莲田千亩,景色优美,蔚为大观。
我们在导游的引领下,过景区高大牌楼,见一道仿古长廊,右侧荷塘,其水清浅,有绿荷浮于上,红*白各色荷花,贴水面而开,是为睡莲,安详恬静,花容秀美,令人联想起正在憩息的娴雅美女。于渡口登上轻舟,沿宽阔的水渠向前,两岸楼宇相连,岸边有男垂钓,有女浣衣,岸上绿树与水中翠荷映衬其间,一派江南水乡景象。
轻舟过两座拱桥,水面豁然开阔,于右前方弃舟登岸,过一古雅的徽式建筑,便是陶辛水韵的核心景点香湖岛。有客问曰,门上牌匾为何叫“胭脂渡”?导游说,据传三国时期,周瑜英年早逝,其娇妻小乔归隐于此。小乔每日临水梳妆,脂粉散落于湖中,故得名“胭脂渡”。又说,小乔常常思念周郎,泪水滴入湖中,化作朵朵白莲,佳人终乘白莲而去,与周郎相会。“佳人踩莲去,碧湖存香影”,“香湖”由此得名。这当然只是一个凄美的传说,但也为景区增添了几分促人遐想的古风遗韵。
令人叹为观止的,便是周遭那密布的莲田了。沿巨彬夹道的小径前行,两边皆绿荷,密密匝匝,连绵不断。至小径尽头,眼界大开,莲田广阔,漫无边际。时值仲秋,虽不见荷花映日,却有莲叶接天。随导游穿行于一望无际的碧绿之间,但见有亭榭、长廊、拱桥、茅屋点缀其中,野鹜惊起于水面,白鸥展翅于半空,环境古朴幽雅,野趣诱人。极目而望,水天相连,白云飘翥,清秋寥廓,怎不令人心旷神怡,宠辱皆忘?朋友大赞,此处真乃仙隐之地!
据导游介绍,北宋大观年间,大诗人陶渊明后裔自江西迁于此地,率众筑堤围垦,始有陶辛大圩。圩内沟渠,全长百里,水系纵横交错,呈八卦形分布,进入圩区,如入迷宫,为古代水利工程之罕见。由此可见,抛弃愚公移山之旧思维,选择适合生存之地而居,自古而然。《左传》有言,“良禽择木而栖”,何况人乎?靖节先生若隐居于此地,恐怕就不至于“饥来驱我去,不知竟何之”(陶渊明《乞食》),而是可以远离尘嚣,乐享幽居之美。先生的莲花神圣高洁,香远益清之气,大概就不仅因“独爱菊”而有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之名句,可能还会早周敦颐数百年,写出陶版《爱莲说》了。
香湖岛为全国品种最全的景观荷花基地之一,据称有数十个品种。陶辛人于此地之外,又辟有莲花培植园,且配有专家,从事研究管理工作。我们随专家而行,听其介绍,不但知莲花名目繁多,而且可以食用,可以入药,更可以观赏,其中学问不浅。最令我瞩目的,是那碗状的莲蓬。荷花于五月盛开,而今花季早过,其子渐熟,那团团莲叶丛中,多有一茎亭亭,高擎结子饱满的莲蓬,似乎在向世人展示着它们结出的硕果。专家为我们每人采撷数个,剥子品尝,鲜嫩微甜,口感甚佳。来自北京的朋友,竟有舍不得吃光,欲捎上几枚,回京供家人品尝者。
嗟夫,人常以“春华秋实”自励或自诩,而莲花,夏显其华,秋结其实,不正是积极向上的人生写照吗?时值深秋,荷塘仍一片碧绿,且仍有少数莲花,不惧肃杀秋风,顽强开放,不正如人间虽至暮年,仍葆其青春之心者吗?有感而发,遂有顺口溜一首:“深秋荷塘尚含绿,残存莲花犹飘香。休叹人生晚境至,老马奋蹄莫彷徨。”
听导游介绍,陶辛镇为全国改革发展试点镇,景区众多,值得一游。但因时间有限,一时不可尽览。待到来年端午节,再来参观美丽乡村,看龙舟竞赛,赏荷花盛开。
来源:年12月7日《中国社会报》
原标题:《王祥夫:梅的好
《孺子牛》文学副刊5则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