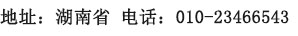清明之于童年,是放歌踏青,追逐春天;也是风清景明,慎终追远。它是节令,也是节日,让孩子既存喜,也生愁。
这个清明,孩子们和作家们一起,穿越时空,以文会友,寄情字里行间,带着我们赶赴一场清明文化之旅。
清
明
●
食
素舂柔艾捣砧忙,墨玉生香儿乞尝
每逢过节,吃什么,是孩子最关心的。清明的吃食,也是“节日限定”,与春天的野菜分不开,与故乡的人事分不开。回忆清明,你是否也口齿生津呢?
清明前后扫墓时,有些人家——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——用*花麦果作供,但不作饼状,做成小颗如指顶大,或细条如小指,以五六个作一攒,名曰茧果,不知是什么意思,或因蚕上山时设祭,也用这种食品,故有是称,亦未可知。自从十 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,不复见过茧果。
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,俗称草紫,通称紫云英。农人在收获后,播种田内,用作肥料,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,但采取嫩茎瀹食,味颇鲜美,似豌豆苗。花紫红色,数十亩接连不断,一片锦绣,如铺着华美的地毯,非常好看,而且花朵状若蝴蝶,又如鸡雏,尤为小孩所喜,间有白色的花,相传可以治痢。很是珍重,但不易得。中国古来没有花环,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。
——周作人《故乡的野菜》
在我们这儿,过清明,就会做清明馃,清明前后,家家都会飘出蒸清明馃的独特味道。
做清明馃,就要用到“青”,也叫“艾草”。这青是在长满杂草的田里长出来的,细细一闻,会有股香气,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辨别的。
摘完回家,就先叫来家中老小,一起“奋战”,把那青上的死叶子摘下,再把它分成一片一片的叶子,用清水冲洗干净,接着把它们倒入大锅中,添上水,慢慢熬,这青在锅中懒洋洋的,从锅底冒上来的气泡是它们的呢喃细语,那从水面上升起的一缕缕热气是它们的喟叹,仿佛泡了个舒服的热水澡。
等水从透明变成墨一般的绿时,就“大功告成了”,大人们把青捞出,挤出里面的汁水,就能和面了。把那青的汁水与面混合。揉面,炒馅儿,开包,一切井井有条,包完了,就上锅蒸熟,放入冰箱。
——*雨凡《清明》
(学生习作)
清明节 的习俗应该就是吃青团子了!主料是糯米粉,配上豆沙馅儿,一口咬下去,软软糯糯,清甜不腻,回味起来有股淡淡的却又悠长的艾草香气。
将艾草汁混入糯米粉做成面胚,包入豆沙馅,放到灶里头蒸,让水躁动起来,使得团子也开始升温,飘出阵阵清香。灶里的一切让人只能猜想:柴已经烧成炭了吧,水已经沸了吧,青团已经软软糯糯了吧?要是皮儿撑不住破了,馅儿会流出来……
香味四处飘散,可以开锅了。
刚出锅的团子,一口咬下去,仿佛就是 啊。
——许蔡杰《清明节》
(学生习作)
我对扫墓没什么兴趣。“吃”才是我的一大兴趣爱好。说到吃,寒食寒食,说的全是冷食,冷冰冰的食物,让人没有胃口。可清明馃和青团却是例外。拜完祖先,奶奶就端上一碗清明馃。清明馃的馅儿五花八门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咸菜豆腐干馅儿了。咸菜啊,热的下饭,冷的爽口,都很美味。尽管吃冷食,也很有滋味。一口咬下去,艾叶微苦,咸菜很鲜,两者碰撞在一起,油还滋滋地窜入口中,啊!真是 难得几回尝啊!
清明节的另一种美食,就是青团了。喜欢的人也是很多。
青团是一个小小的团子,周身有糯米点缀,样子比清明馃小巧,也精致很多。青团包甜豆沙馅儿的居多,并不油腻,尝一尝,甜香四溢,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再或者,可以配上醋、白糖和酱油等,使人忍不住要多吃几个团子。
——郭璟玥《浙江的清明》
(学生习作)
清
明
●
游
了却坟前祭扫事,南国春半踏青时
清明时节“借墓游春”,是不少人的心声,大家兴致勃勃,笑语晏晏。回忆儿时清明,也多是一幅明亮的春日画卷吧。
丰子恺《清明》
清明三天,我们每天都去上坟。 天,寒食,下午上"杨庄坟"。杨庄坟离镇五六里路,水路不通,必须步行。老幼都不去,我七八岁就参加。茂生大伯挑了一担祭品走在前面,大家跟他走,一路上采桃花,偷新蚕豆,不亦乐乎。
到了坟上,大家息足,茂生大伯到附近农家去,借一只桌子和两只条凳来,于是陈设祭品,依次跪拜。拜过之后,自由玩耍。有的吃甜麦塌饼,有的吃粽子,有的拔蚕豆梗来作笛子。蚕豆梗是方形的,在上面摘几个洞,作为笛孔。然后再摘一段豌豆梗来,装在这笛的一端,笛便做成。指按笛孔,口吹豌豆梗,发音竟也悠扬可听。可惜这种笛寿命不长。拿回家里,第二天就枯干,吹不响了。
祭扫完毕,茂生大伯去还桌子凳子,照例送两个甜麦塌饼和一串粽子,作为酬谢。然后诸人一同在夕阳中回去。杨庄坟上只有一株大松树,临着一个池塘。父亲说这叫做"美人照镜"。
叶圣陶《过节》
几个孩子有时跟着拜;有时说不高兴拜,也就让他们去。焚化纸锭却是他们欢喜做的事情,在一个搪瓷面盆里慢慢地把纸锭加进去,看它给火焰吞食,一会儿变成白色的灰烬,仿佛有冬天拨弄炭火盆那种情味。孩子们所知道的过节, 自然是吃饭时可有较好较多的菜;第二,这是家庭里的特种游戏,一年内总得表演几回的。至于祖先会扶老携幼地到来,分着左昭右穆坐定,吃喝一顿之后,又带着钱钞回去:这在孩子是没法想像的。
胡泽宇《清明小记》
在我的印象里,清明从来不是雨蒙蒙雾凄凄的,相反,田间草绿芽嫩,山间叶翠花俏。
一行三人先祭拜的是曾祖父和曾祖母。那坟在半山腰,沿途都是各色的耕田。难得的是坟旁有山泉——不过涓涓细流,在不远的山脚徘徊成一方小水潭。
压*纸,摆祭品,继而烧纸钱。每到这时,我就抖起精神细观风向,及时调整站位,力求站稳上风口,不沾染一丝烟火。但往往事与愿违,风甚是喧嚣,三百六十度环绕着吹,差点把我逼上山顶。
爷爷的坟在一片竹林旁,修葺得很是精心。石梯五六阶,青松戍左右,藤蔓爬满了四周的砖墙——藤蔓是不请自来的,见缝就钻,但不懂见好就收,喜欢越界,父亲拿着一把短镰哧嚓哧嚓地清理藤蔓,但人一走,它们又会幽幽地缠绕上来。
两边祭拜结束,母亲便兴致勃勃外出踏青,不是下田剪野菜,便是上山挖春笋。有时还拉上无奈的父亲充当搬运工。留下的我学老僧入定,懒在椅子里背对太阳,看青烟袅袅从影子头顶升起。
清
明
●
思
少年初识伤心味,悠悠香火念故人
清明时节,不由得就会想起生命中逝去的重要的人,想起参加他们的葬礼,想起当时内心的伤痛。不知不觉,儿时的我们对“生命”就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敬畏。
走了很长一段路,弯弯曲曲的山路就像大家弯弯曲曲的心,哀哀戚戚的鼓声与唢呐声环绕在耳边。到了山上,每个人都向墓碑拜了拜,拿了一些硬币,将钱丢进洞里,然后再拜一拜,便下山去了。爸爸依旧没哭,脸却僵得如同百年老木。
我们又来到村子的空地上,中央架了一座天桥,旁边有打快板的和唱戏的。没等我弄明白,音乐响起,我随着人流走上天桥,但旁边的人一开始唱戏,我们便要停下不动。我向后瞟了一眼,却惊觉父亲已经泪流满面。
回家的路上,我又想起了奶奶,想起她给我留过期的酸奶,想起她给我夹喜欢的瘦肉,想起她拦着生气的爸爸把我护在身后的样子……
奶奶很大很大,装下了我的整个童年;奶奶又很小很小,躺进了一方矮矮的坟墓。
——傅锦晨《那个难忘的葬礼》
(学生习作)
爷爷去世了。那是我 次参加的葬礼,到现在也不能忘记。
爷爷年轻时为了救火受过伤,年纪大了又得了病,但他总是笑眯眯的。可我见他 一面时,他躺在床上,身上盖着白布,慈祥的脸也被蒙住了,只露出树枝般干枯的手和脚,颜色微微发青,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。他平时抚摸我头发的手,正被姑姑紧紧握着。大人们都在床边哭,我在门口悄悄看了会儿,怎么离开的已经记不清了。
我看见姑姑和爸爸把盒子搬进了一个石洞里,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爷爷了,也不会有粗糙的大手抚摸我的头了,我不由得鼻子一酸,问妈妈:“人为什么会死啊?”妈妈没有回答,她也哭了。
回到爷爷曾经住的老房子,大人们都要守夜。我和哥哥打着地铺,葬礼上的一切拼凑成光怪陆离的梦,我突然觉得有些喘不上气。
爷爷的葬礼,我到现在也不能忘记。
——金乐妍《葬礼》
(学生习作)
阿梅婆婆瘦小的身躯静静地躺在老屋里,脸被白布罩住,全身苍白,也就那寿衣是婆婆身上最鲜艳的。随后,一个身着奇怪衣裳的人出现了,一边说着什么,一边在婆婆遗体旁走来走去。她说一句,大人们回答一句。我虽不懂为什么要请这样一个人来,但听着听着,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下来了。
仪式完毕,阿梅婆婆的遗体被放上灵车,灵车黑黑的,令人心生害怕。灵车开在山路上,十分缓慢,我们在后面跟着。鞭炮声、哭喊声响彻了这个中午,我禁不住捂住耳朵,默默地流泪,再看一旁的妈妈,已哭得说不出话来了。
死亡,一个多么恐怖的字眼,活着的人泪如雨下,悲痛万分;而逝去的人,可能只是淡定地迎接一场长眠,去往天国,或许她还陪在你身边,默默守护着你,悄悄对你说:“我在这儿呢,你们别伤心,别挂念我。”
——郦科夷《 一程》
(学生习作)
这个日子,给了人放纵感情的一个理由,尽可以让我们逐着思绪去天边飞,如同那些牵线的风筝,无论在天边、树梢,还是落进池塘,远远近近,总会有一根线,叫作清明。
图文:胡泽宇
审核:楼上工作室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#个上一篇下一篇